触乐怪话:巨物恐惧症
触乐怪话,每天胡侃和游戏有关的屁事、鬼事、新鲜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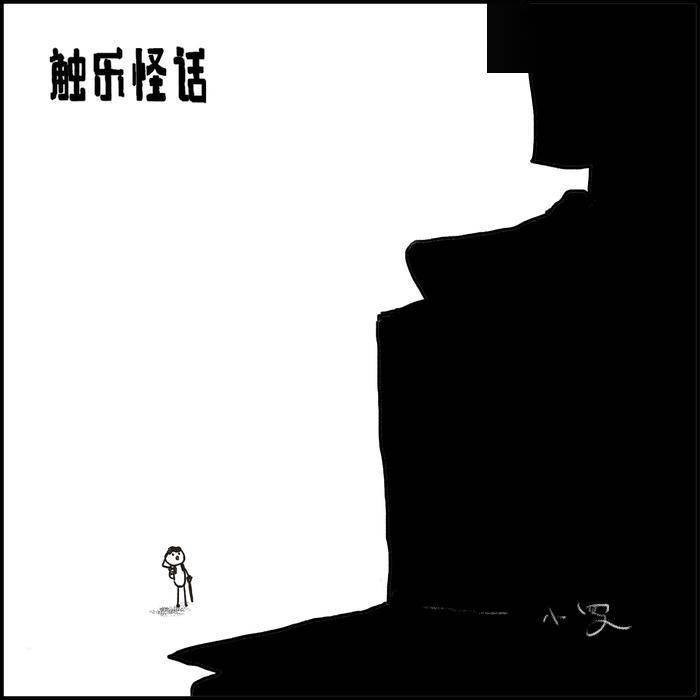
图/小罗
这几天我一直在上海出差,整体来说都是围绕着Bilibili World(BW)来的各种活动和访谈。置身在拥挤的人潮中,艰难地往返于各个场馆以及……在人流中迷路。每天超过2万的步数让最近缺乏运动的我找到了恢复训练的痛苦,相信每一位有热情来BW的观众都能感同身受。也因此,我对这个庞大的建筑产生了十足的兴趣。
BW的场馆位于国家会展中心,这是一个从高空俯瞰像四叶草的巨型建筑,根据官方宣传,总建筑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。这个数字本身没有意义——直到你亲身走进它。
走进去,数字变成了空间。从一个展馆到另一个,要穿过一条条极长的、有楼顶覆盖的柏油路面。炙热翻涌的空气从廊道里穿过,我才能切实地感受到展馆空调的牛×之处。人一多,注意力就必须集中在目的地上,一个精确的目标,从A到B的任务,困难则是穿越拥挤的人潮,要不然我很快就会感到焦躁。在这种目标下,身边的人群变成了移动的色块。

BW展馆还不是“四叶草”里最高的那个,震撼之下,我忘记了拍照
我和所有人一样,是这个巨大身体里的一个细胞,沿着固定的脉络随机流动。迷路在人潮中的感觉和平时不一样,更像是一种在庞大空间里失去自身坐标的漂浮感,像漂在海上,稍不注意就会被浪推走。受不了把注意力放在人群,我抬头看向高高的天棚,仿佛这栋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城,而我们只是其中的临时居民。
这种体验很矛盾。一方面,我会惊叹。如此巨大的空间,由钢铁和水泥构成,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它有一种压倒性的美,让人产生敬畏;但另一方面,一种微小的焦虑感会爬上心头。我感觉自己很渺小,仿佛随时会被这个空间吞没。这种感觉,或许就是大家常说的“巨物恐惧”的边缘——它不是那种让你尖叫逃跑的恐惧,而是一种面对无法理解的庞大时,本能的退缩和好奇。我看着它感到眩晕,又忍不住想抬头看,看清楚它的构造,每一根悬梁、每一盏灯、每一个空调出风口……
我幻想着自己正站在容纳万人的场馆中央,身边的一切都消失了,没有人、没有展台、没有声音,只有无数盏星星一般的白炽灯在空中挂着,就像电影《2010:太空漫游》中的那句经典台词:“My god,it's full of stars……”
扯得远了点,但这个感觉我总觉得似曾相识,但又想不到具体的场景。直到现在,我正坐在上海虹桥机场里写这篇怪话时,我找到了具象化的回忆——北京大兴机场。

飞机你往哪开?
那是一次延误许久的深夜航班,落地至少在11点30分以后,因为已经没有地铁。我已经记不清那天有什么事情,我落地后一直待在下飞机的地方没有走,和友人打了近1个小时的电话,那时,身边所有的人都已经离开。
大兴机场的设计很有趣,是一个海星状的建筑,印象里,你很难在大兴机场找到一个直立的柱子,只有巨大的C形立柱像生物的骨骼一样伸向屋顶,汇入航站楼的中心。设计师曾表示,这种放射状的“海星”布局是为了效率,让旅客从中心到最远登机口不超过8分钟。那天夜里,我拖着行李箱在无人的大兴机场走了许久,与旷野中的漫步不同,在一个极度现代化的机场里,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近乎无限的自由,和一种与在国际会展中心里同样强烈的暴露感。
突然想到,我很早就加入了一个豆瓣小组“BDOER巨大沉默物体迷恋者”,刚刚翻回去的时候发现,这甚至还是我关注的第一个豆瓣小组。我翻了一下他们对这个概念的定义——“于小组定位而言,例如对建筑来说,只有科幻电影或者空想艺术里的巨型建筑才算BDO,现实世界里普通的(非异形)高楼大厦并不算在其中。除非是造型别致的类似苏维埃宇宙主义极权建筑、巴黎乌托邦建筑、香港九龙城寨等,注入了意识形态的异形巨建。正如普通天象不算,极端气象才算,普通山峰不算,克苏鲁中疯狂的山脉才算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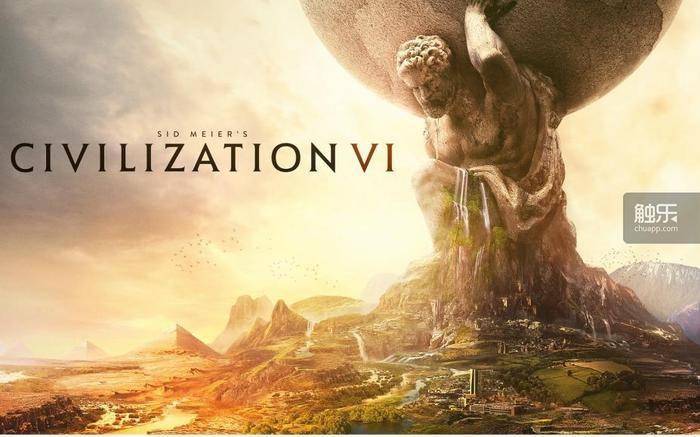
《文明6》的封面就很有那种巨物感
嗯……我不太喜欢组长的说话方式,不过没人在乎,我自己也不在乎。我还是用“巨物恐惧症”来描述这种时而敬畏、时而焦虑的心态吧——当一个物体的大小远远超出我们日常的认知范围,大脑似乎就难以处理,从而触发了原始的警报。心跳加快,手心出汗,但同时又有一种病态的好奇心,驱使你继续观察。这很好地解释了我面对这些建筑时的状态:一种夹杂着恐惧的观摩。
我开始想起那些超越使用功能的建筑。就像历史上的金字塔、大教堂和纪念碑一样,它们实则是权力和国家(统治者)意志的体现。在国家叙事里,这些巨型建筑也是实体的里程碑,是技术实力、经济成就和民族自信的宣告。就像“文明”里的奇观,是写给世界看的宣言。
所以,当我感到自己渺小时,或许这种感受本身就是设计的一部分。建造者们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这种力量——个人的渺小,反衬出集体的雄伟。
可我想要的,还是能在其中安放自己的那个小小的、符合人性的角落,可能只是一个刚被太阳晒过的座位。
